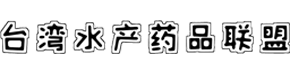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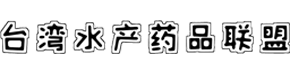

我喜欢蘭屿。
最初是喜欢这个名字。蘭这个字,一定要是繁体字才会显得特别有韵味,有一种繁复的对称的美感,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刺绣,。然后用熨斗烫出熨帖平整,方方正正的一个蘭。简体的兰就很无趣,像平铺直叙的三条铁轨,任你一眼就望到了头。
蘭屿是台湾的一个外岛,坐落在太平洋里,被称作太平洋中的一颗深邃宝石。属于台东县,按行政区划来讲属于蘭屿乡。它的纬度和最南的垦丁也差不太多,总体来说应该是热带气候。因为散落在太平洋里,和本岛来往较少,所以众多外岛中,唯独蘭屿保持着野生与纯粹。岛上椰风蕉雨,一派热带风光。分为六个部落,住着原住民,仍然保留着传统和原始的生活习性。即使台湾人也鲜少去蘭屿,因而更平添一份神秘。
发呆亭与象棋
十月上旬,我和朋友相约来到了蘭屿。
客船从台东的富冈渔港出发,在汪洋大海里行驶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蘭屿有两条公路,一条环岛一周,约37km,沿路分布六个原住民聚居的部落,另一条横跨盘踞在岛屿中部的大山,将岛屿东西海岸的部落连接起来。
行程前几天我们住在西海岸的渔人部落。白天我和朋友在烈日下骑脚踏车环岛,到了晚上朋友都早早回民宿休息,我则一个人留下来盘腿坐在发呆亭里看海。
发呆亭是一种简易的凉亭,在环岛公路上随处可见,木板拼接起来的地板,四周立上四根支柱,顶上用两块木板搭成三角形,给发呆亭盖上一个帽子。岛上为何遍地发呆亭,我想可能和变化多端的天气有关。海岛上忽晴忽雨,常常一阵风吹来一片乌云就会刹那间落下一场急雨,部落间又相隔甚远,在外赶路的人找不到屋檐躲雨,只得像古代车马驿站一样修起一个接一个的亭子临时避雨。一场雨约莫十几二十分钟,真空的时间里能做的大概只有望着海发呆。
我脱了鞋,光脚踩上去,走到亭子最靠海的一侧,靠着围栏盘腿坐了下来。海就在我不远处,夜里翻滚的浪,像极一条条白色的鲸鱼。天边时不时划过一道闪电,张牙舞爪般将层叠的云朵照的通体发亮。
我把脑袋靠在围栏上,闭着眼睛,把呼吸调整到和潮起潮落相同的频率。
吸。
呼。
吸,
呼。
吸,
“要不要过来下一局棋?”有个声音突兀地打断我的节奏。
睁开眼睛,发现在我对角的地方盘腿坐着一个男生,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他的确是在跟我讲话。
“好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利落起身,两步跨到他面前坐下。
是一副象棋,每个棋子差不多五十元硬币大小。
我们俩很有默契地各执一个颜色,他摆棋比我快,又顺手帮我把棋子布好。
“你要先走吗?”我俩正襟危坐,他先开口。
“其实…….我也就会一点点而已。”正式开始我反倒露了怯,不好意思地冲他挤了挤眼睛,左手食指和拇指相触,比划了个一点点的手势。
“没关系。”他摇摇头,“我水平也就还好。”
我于是深吸一口气,推出去一个炮。炮二平五。果然,他来了个炮八平五。这些基本招式我还是熟记在心的,我于是跳马,他动车。开头还挺顺利,没成想后面我一步错棋,让他接连吃掉我的马和车。
看我连失两员大将,他笑着说“可以让你悔一步棋。”
“不要!”回答地斩钉截铁,我挺直上身,输棋不输阵。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开局不利的我如同一个被戳了一针的气球,横冲直撞地泄气,终于在连输五局之后,啪哒一声掉在了地上。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我挥挥手,双臂用力撑着身子往后挪了一截儿。
“真不玩了?”
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其实你往后几局表现的都还不错。”
我耸耸肩,假装嗔怒,“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就不玩了。”
他呵呵一笑,一边收拾棋子一边跟我讲话,问我是不是从大陆来,来自哪个城市,为什么想到要来蘭屿。我一一回答之后,也开始问他同样的问题。知道他是台湾人,家在台北,大学毕业两年,现在在蘭屿的一所小学教书。“椰油国小,就在离航空站不远的地方,你来的时候应该有看到。”他用手指了指,向我示意那所学校离这儿不远。
为什么会想来这座小岛上教书呢?
“喜欢海呀。”他把身子转向大海,伸懒腰似地展开双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爷爷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
原来如此。难怪会从台北跑来这么偏远的小岛上。
我跟他说我们大陆的年轻人毕业之后都迫于形势急于找一份高薪工作,鲜少像他这样职业选择单纯基于喜好的人,我羡慕他的勇气也佩服他的坚定。
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留下一串爽朗的笑声。
“蘭屿有名的飞鱼你吃到了吗?这里每年还有飞鱼祭,是达悟族人特有的祭典活动,不过你来晚了,捕捞飞鱼的旺季在六月份以前。”他向我介绍道。
飞鱼我当然知道了,和秋刀鱼相比短一点也扁一点。身体两侧有翅膀状的双鳍,可以在海面滑翔。错过飞鱼飞翔的壮观场面,尝尝味道也好。可惜今天专门跑了几家小餐厅,招牌的飞鱼特餐全都卖完,只能空望着菜单上的图案流口水。我瘪着嘴,不开心地摇了摇头。
“那明晚你还在吗?我这里还有几条腌好风干的飞鱼,我带过来给你尝尝。”他看着我,眼睛里亮亮的。
谁会拒绝共享美食的邀约呢?我点头似小鸡啄米,然后抬起头对着他笑弯了眼。
我们并排坐在发呆厅里,姿势一致,双手撑着地板,上半身向后靠,海风夹杂着咸咸的海水吹到我脸上,惬意非常。
飞鱼与夜访,青青草原上的星空
第二天的行程是继续环岛,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公路横贯岛屿东西两岸,从那条路上骑行的话正好可以环岛一半,我和朋友一拍即合。
等到找到那条路的入口,骑出去两百米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条路不是平的。岛上四周一圈是和海平面相接的平地,而中间则是凸起的山地。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并非如原本设想的一般穿越山谷,而是贴着山的轮廓,形成一条抛物线。X轴是地面,Y轴指向天空。换言之,我们要先翻山——骑着脚踏车爬上山,到了山顶再从另一侧爬下来。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好狗不走回头路。硬着头皮也要上。我和朋友四目相对,握紧拳头,悲壮地冲对方点头,然后继续踏上征程。
路上遇到很多骑机车的人,看到推着脚踏车的我俩都表情一致地目瞪口呆,然后冲我们大声喊加油,好歹赢得大家的注目,也不亏。
等到终于从山上下来,脚踏车稳稳地落到环岛路上的那一刻,竟然有种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错觉。
晚上我如约去了发呆亭,亭子里坐着个人,只给我一个黑色的背影,我蹑手蹑脚地往他身后走去,自以为悄无声息,没曾想他突然把头转了过来。
“嗨,你来了。”他冲我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坐这儿吧。”
他拍了拍右手边的地板。
我在他身边盘腿坐下,发现他面前又铺了一盘棋局,连忙摆摆手,“别别别,我输不起。”
他笑的很爽朗,“别怕,我自己玩呢。”然后从另一侧拿出一个便当盒,打开来看,里面是两条飞鱼,飞鱼被剖开翻成两面,鱼鳍贴着身子,果然如翅膀一般。鱼身通体呈银灰色,下面还垫着些白饭。飞鱼是被腌过之后再清蒸过的,配菜是几撮九层塔。
他把筷子递给我,说这些都是我的。我不客气地接过筷子,夹起一块鱼肉。我对食物没什么研究,只觉和秋刀鱼的味道没差,肉质很嫩,有点鲜又有点闲。
我还在拨弄鱼肉,他问我又没有参加岛上的一项传统观光活动——夜间生态导览。“没…….有…….”我拖着长调回答他,试图表现出我的遗憾。同行的小伙伴都对这个兴趣寥寥,我也只好放弃了参与的打算。
“我带你去。”他从兜里掏出一只手电筒,打开,射出一条明晃晃的光柱,细碎的水珠在灯光中跳舞。
跟着他走了约莫十分钟,进了一片山里,他告诉我,这里最有名的特色生物当属角鹄,也就是猫头鹰,和夜光蜗牛。
通往山里的路很逼仄,两旁长满了高低不一的植物,他时而停下来,告诉我这个树木可以用来做拼板舟,那种树是蘭屿岛上独有的树种。置身一片茂盛树林中,身边全是我从未见过的热带树种,那一刻竟突然升起了一股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突然,他半蹲下身子,招呼我靠近一点,我凑过去,手电筒的光聚在一片芭蕉叶样的叶片上,光线的中心是一只白壳蜗牛,软软的身子也呈白色,两条触须呈透明状。原来这就是夜光蜗牛啊,我在心里偷偷地想,我还以为它会在夜里发光呢,真的是徒有虚名诶。
就这么又走了几步,他突然把手电筒照向一棵树,然后让我顺着光线去看树上的角鹄。我用眼睛快速扫描了一边光线区域,却始终没看到角鹄的身影,他急了,扳着我的脑袋给我定到正确的方向,我伸长了脖子这才看到了那只角鹄。它躲在树杈中间,露出了白色的毛绒绒圆滚滚的肚子,过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来,和我四目相对,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一个凶巴巴的人在跟我打招呼“嘿,伙计。”
我们继续往前走,迎面碰上一群也是来夜观生态的游客。领队的人热情地冲我们打招呼,意料之外地是,我居然在那群人里发现了之前偶遇过一次的漂亮小姐姐,她看到我和象棋小哥一起走,冲我狡黠地挤了挤眼睛,拿出自己的相机说要帮我们拍照,他还在另外一侧摸索,我对着小姐姐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偷偷挪到他背后,比了个耶的手势。
“这是胶片机,所以照片等我回上海之后洗出来再拍照发给你。”小姐姐和我挥手再见。
从山上下来,我们又走到环岛路靠海的一侧,去探索潮间带。他补充说很多生物都有夜行的习性,因此晚上来会比较容易看到它们的行踪。海边的礁石很不好走,看我走的摇摇晃晃,他走过来,伸出胳膊,让我抓着他。夜里的海边只有我们两个人,头顶是漫天的星星,耳边是海浪拍打礁石一波一波由远及近的声音,我们都没有讲话,就这么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走着,忽然觉得心里一下子变得十分开阔,像是对整个世界敞开了心扉。
走到潮间带附近,一边走他一边指给我看各种海洋生物,寄居蟹、虾、海螺、海胆,各种我只在海产店里见过的生物。好饿哦,正想着,我的肚子很应景的咕咕叫了起来,他见状笑个不停。
“飞鱼饭都给你吃了还没填饱肚子哦?”
他让我先停下,说要找个东西给我看,等到他神神秘秘地走过来,把手伸到我面前,然后把手电筒的光打到手上的一瞬间,我吓的尖叫起来,本能地退后一步,没成想脚下打滑一屁股坐在了礁石上。
“啊啊啊啊啊啊”,我的惨叫声以一个与海浪声不同的频率打破了海边的宁静。
他见状连忙伸出手过来扶我,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冲他摆手,“别别别,你先把你手上那玩意儿丢掉。”
那是一条蛇,大概有小拇指粗,二三十厘米长,蓝白相间的花纹,鳞片在手电筒的光下格外耀眼,它扭动着身子,顽强地和捏住它的手指对抗。我天生畏惧这些软软的光溜溜的生物,看着它宛如看到一个扭动的噩梦。
我坐在礁石上,抬起头看向天空,夜色宛如一块巨大的幕布,星星如钻石般点缀其上,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们真的一闪一闪。
“我带你去青青草原上看星空吧,那边海拔更高一点,视野也更开阔。”
青青草原就在环岛路边,是一片大草地,站在边缘往下看,悬崖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躺在草坪上,离星空更近了一些,视野果然很好,整个夜空就这么平铺在我面前。我现在正身处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眼前是我从未看过的风景,虽然这里海拔很低但我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要更接近这片天空,我甚至觉得自己与天空,与海洋,与整个世界融为了一体,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知到了自己的存在。我拥有整个世界就像世界拥有我。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我只知道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哭并且眼泪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掉下来了。
你还会再来吗?他躺在我旁边,歪过头来,看着我。
嗯。我用力地点点头。
“下次来我们再一起下棋吧。”
“那我回去可要苦练棋艺了。”我信誓旦旦。
“一言为定。”
他伸出手举到半空,我也举起手,在空中清脆地击了个掌。
陌生人与芋头冰
第三天骑脚踏车路过一家叫做雯雯冰品的小店,小店开在环岛路边,布置得像酒吧吧台,不过是露天的而已。三四个木制长凳刷成天蓝色,排成一排。正好到了傍晚,太阳落到了接近海平面的位置,天空被分隔开像一本摊开的书。上篇是夹着丝丝缕缕白云的蓝天,下篇是层层叠叠由深入浅的橘色,一直蔓延到与海相接。落日耀眼的光芒在海面上铺成一道长线,细碎的金色光点随着波纹欢快地跳跃。
我点了一份招牌咖喱猪肉倥饭,一边吃一边和朋友聊天。味道和在别处吃的也没差,只是因为不喜欢猪肉,都剩在了盘子里。
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条黑狗,从我吊在半空的腿边蹭过,仰着头冲我摇尾巴,眼睛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我的盘子,满是期待的样子。
“你想吃肉了吗?”我低头夹起一块肉,在狗狗面前晃了晃。
“不可以喂食物给狗狗哦。”一个陌生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我抬头,是坐在我旁边的男士。大约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皮肤也黑黑的,有点像余文乐。
我问他为什么,他跟我解释,人类的食物经过烹饪,里面的一些盐分会给动物的肾脏造成负担。
我点点头,把筷子放回了盘子里。
“我见过你。”他笑了笑,对我说。“你骑脚踏车环岛对吗?中午有路过青青草原对吧?我正好在旁边歇息。对你印象深刻。”
哈,真巧。
“这家店的芋头冰非常有名,有吃过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他打了个响指,让老板拿过来三份芋头冰。“请你吃。”
芋头冰的味道很不错,绵密的冰里裹着一粒粒饱满的芋头果肉,冰沙入口即化,芋头落到嘴里很有嚼头。我捧着小碗转身背靠着吧台坐着,面前是无边的大海。凳子很高,我勾着双脚把双腿悬在半空晃啊晃。太阳慢慢掉下去,晚霞升了起来,天空从金黄色变成了粉红色,像沐浴在童话故事中。
凉凉的晚风,海边的小店,小店里橘色的灯光,吧台上悬着的风铃,白墙蓝椅,透明的小碗里盛着香芋色的冰,旁边的长凳上几个游客,白色的背心和彩色的吊带,远处粉色的晚霞如同日本电影里带着柔光的镜头,这一切太符合我对海边假日的想象。
我一边舔着芋头冰,一边偏过头问他,“你也是来旅游的吗?”
“不,”他伸出食指摇了摇,“我在这边当老师。”
“哇!那你认识一个叫”我急急地想要问他是否认识那个男生,话到嘴边才意识到我竟不晓得他的名字——我从来没有问过。
他冲我挑了下眉毛,似乎在等我把话讲完。于是我告诉他我遇到了另一个男生,也在这边当老师,我们还一起在发呆亭下象棋,还带我去夜观生态。他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反而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潜水,爬上气象台观海,然后继续环岛,看看一路会有什么奇遇。“我这个人做事向来没什么计划,何况岛上这么美,就是坐在发呆亭里发一天呆都让人梦寐以求。”
“那我倒是可以推荐你几个地方去玩。”他拿过吧台边上的一张岛上的地图,指给我一个叫做蘭恩博物馆的地方,告诉我这里会有专门安排的原住民介绍岛上的历史发展和人文风情。“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不要错过。”
蘭恩博物馆与做木工的老爷爷
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骑着脚踏车出发继续环岛,行至中途,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正巧旁边有一个大院,正门由两个相对的拼板船组成,白色的船身,边上一圈红黑白三色花纹,船头的位置高高翘起,顶着由几个圆片构成的装饰。
我猜就是蘭屿余文乐口中的蘭恩博物馆。我和朋友相视一笑,择日不如撞日,看来是老天爷想拉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穿过大院径直走到挂着博物馆牌子的房子面前,推开门,迎面一个皮肤黝黑的男生微笑着走过来,自我介绍是这里的馆员。他指着旁边一位老人跟我们介绍说等下十点钟这位原住民爷爷会带领我们参观外面的地下屋,之后会带我们上楼介绍馆藏和达悟族的民俗风情。
“现在九点半,”他扬起手臂看一眼手表,“你们可以先在一楼看看这些工艺品和纪念册。”
一楼像一个简单的文创小店,三两个货架上零散地摆着一些手工艺品,黑白红三色绳子编织的手链,彩色珠贝串起来的项链,印有达悟族特色图腾的小手提袋,还有一些斜靠在一起的摄影集。我的手指依次划过这些小件儿,最后在一个木雕旁边停了下来。那是一只拳头大小的猫头鹰,看起来脱胎自一整块小木头。一对大圆眼睛占据它身体的三分之一。小刀经过的地方留下粗糙的刻痕,反而显有一种未经雕琢的天然。
馆里的男生走过来,跟我说这个木刻作品来自角落那位爷爷。顺着他的指引我看到了坐在门边上的老人,他手握一把小刀,弓着腰低头正忙着刻一块木头。我走过去,在他的面前的长椅上坐下,伸长脖子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老爷爷抬起头冲我一笑,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他一边继续刻着手中的木头,时不时抬头饶有兴趣地和我攀谈起来。他问我中国大陆现在什么样,和台湾有什么不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蘭屿,还说蘭屿其实应该属于菲律宾。他嚼着槟郎,讲话的时候嘴角红色的汁液像血,偶尔掺杂几句当地的方言,两个耳朵都不怎么好使的人进行了50%的交流,期间我还唱了一首国歌给他听。
十点整的时候,他的作品完工了,是一个小小的猫头鹰,比货架上那个更小一点,胖嘟嘟圆滚滚的身子,依旧活灵活现。
老爷爷起身带我们去参观地下屋——蘭屿特色的建筑。地下屋建在一片人工挖掘的凹地里,外围垒石成墙。之所以建在地上,是因为蘭屿石全世界著名的多风地区之一,堪称风岛,为了躲避风灾,达悟族人巧妙地设计了这种建筑结构。沿着石阶下到地下屋里,会发现整个建筑都是木质结构,木制的隔板上自然也少不了三色花纹和船眼图腾,小木屋的顶梁山横着一个木杆,上面挂着动物的头骨,大概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多寡。老爷爷拉我们进去,告诉我们哪儿时爸爸睡的地方,哪儿是妈妈和孩子睡的地方。
“像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就不能睡在家里咯。”他跟我们打趣道。
那我们睡哪儿?我和朋友面面相觑。
“当然是外面的发呆亭咯。”老爷爷一手指着外面,咧开嘴巴笑个不停。
博物馆在我们先前去的那栋建筑的二楼。一进门的地方摆着一个拼板舟,旁边站着一对穿着达悟族民族服饰的男女,女士脖子上挂着大片珠贝和红色玛瑙串起来的项链,男士的特色则是和头顶漏斗般的银盔。再往里面沿着墙壁摆了一排玻璃橱窗,橱窗里摆着达悟族人常用的工具和杯盘锅碗。我向来空有逛博物馆的心,真正听起讲解来却总是左耳进,出门之后就把老爷爷介绍的内容忘的一干二净,唯一念念不忘的是那串珠贝串成的项链,银白色的贝壳上泛着五彩斑斓的光,彻底俘虏了我的一颗少女心。
送我们出博物馆的时候,馆员小哥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小秘密。
原来,那位原住民爷爷的女儿早年嫁给了一个来自大陆的男人,那个男人带着这个姑娘离开蘭屿定居在了台北,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独自回到了蘭屿,留在这里当了一名国小教师。可惜,在蘭屿呆了没多久,就为了救一位落水的游客丧生在了海里。
他指着院外环岛路一侧的海,说,事故发生的地点就在那边。而这位爷爷之所以留在这里做一名讲解员,其实也是为了离他的孙子近一点。
我回头转向那位爷爷的方向,回忆起他低头刻猫头鹰时专注的神态和动作,突然觉得那每一条刻痕里,大概都藏着他对孙子说不出口的爱。
天空的眼睛与东清秘境
那天晚上我们离开渔人部落去了东海岸的东清部落,我在那里定了一家超贵的民宿,叫做“天空的眼睛”,坐落在东清湾边上,透过房间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太平洋上第一缕曙光。
第二天我差点没被朋友打死。因为那天天公不作美,太阳好巧不巧被一片乌云挡住,等到该死的乌云终于逃开,太阳已经快升到半空了。
但我仍然记得,那天晚上三点多,我从床铺上爬起来盘腿坐在落地窗前,海风大的异常,怒吼着席卷而来,带着摧枯拉朽的架势,大片大片的云成群结队地从头顶驶过,房间外面被月光照的明晃晃的热带植物在海风中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东倒西歪任其摆布。我好像偶然穿越回到史前世界,以上帝视角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风云变幻,目睹着这个世界的形成与演化。这种感觉,真的是奇妙到无与伦比难以言喻。
傍晚我和朋友一起去了东清秘境。所谓秘境其实就是海岸边由礁石围起来的天然坑洞,因为藏在礁石下面不易被发现故而称为秘境。傍晚涨潮的时候海水会从一侧灌进洞里,被礁石过滤过的海水极其清澈,随着深浅变化从浅绿色过渡到蓝色。海水退潮的时候还会留下许多五颜六色的小鱼,和各种颜色的贝壳珊瑚,脱下鞋子踩进水里,随手一抓都能捡到很多宝贝。
我换上泳衣,踩着海边的礁石寻觅了好久才找到秘境的入口,手脚并用抓着礁石慢慢爬下去,看到洞里的第一眼就被彻底征服了。浅绿色的海水澄澈的就像一个梦。阳光落在水面上形成菱形光圈,随着海水的起伏摇摇晃晃。我浮在水面上,希望可以把这一刻永远存档在我的脑海中。
渔港
我们搭早上十点那班船离开蘭屿。
开元渔港很热闹,好几艘船停在渔港边等待调度,渔港的另一头,一伙年轻人在玩跳海,他们跳下去又爬上来,乐此不疲。
登船之后,我左顾右盼忙着找洗手间,一位穿着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看起来也是岛上的原住民,他听到我找地方洗手,于是走到我面前来,让我伸出双手,我照做,然后他也伸出双手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们俩相视一笑,觉得他真的好调皮。
等到落座,我后排的座位上正好坐着在岛上两次遇到的一个姐姐,她说我俩太有缘份,约我回台东后一起吃饭。
兰屿不大,三四天里常常会和遇到的人再次碰面。但我知道,当船驶离这座岛屿,有的人就再也见不到了。
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所以我们把相遇叫缘分,叫邂逅。这个词太浪漫了,浪漫到要用一部爱情小说来做注解,浪漫到值得为此写一部爱情小说。
船快要开动了,悠长的汽笛声缓缓地响起。我喝完晕船药,把瓶子塞进包里,抱着包把脑袋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离开这座岛屿了。我还会再回来吗?
发呆亭、象棋、飞鱼饭、芋头冰、嚼着槟郎的爷爷、木刻的猫头鹰、青青草原上的星空、和我一起看星空的人。它们依次从我眼前闪现,就像海浪一波一波拍打在窗玻璃上,留下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
再见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受到手机震动了一下,掏出一看,是一条line的新消息。来自蘭屿余文乐。
“你搭上船了吗?”
“上次你说和你在发呆亭下象棋的男生,是这个人吗?”
海上网速不好,照片加载不出来,药劲儿上来,眼皮沉得厉害。我把手机放下,闭上了眼睛。
关于他的问题与答案
“他叫陈逸丞。蘭恩博物馆里那位爷爷的孙子”
“两千零八年那年,他来岛上做老师。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他在发呆亭一个人下象棋的时候听到下面有人呼救,于是跳下海去救那个女生,然后被海浪卷走了。”
“他很爱坐在那边独自一人下象棋。所以那副棋我们一直给他留着。”
“之前不想你害怕,所以一直没敢讲。旅途愉快,以后有缘再见了小姑娘。”
图片加载出来了。照片里,他盘腿坐在椰油国小的跑道上,两个小男孩用胳膊勾着他的脖子,趴在背上。他笑容很灿烂,唇红齿白,他皮肤很白,和俩黝黑的小男孩有鲜明的色差。
我灵机一动,拿出手机点开Facebook搜索这个名字。同名的人不少,我挨个点进主页去看,但都不是他。大约翻了三页后,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是达悟族的船眼图腾。强烈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一定是他,我欣喜若狂地点进去,看到最近一条消息的时候,我惊呆了。
那条消息发布于2008年5月,只有一句话,“耗时一个月终于完工”,加上一个耶的表情。对应的照片里是一只木头刻出的小猫头鹰,圆圆的脑袋,笨拙的大眼睛,和蘭恩博物馆里那位原住民爷爷手上拿的猫头鹰一模一样。
再往下翻,是几张小孩子的照片,看得出来拍摄于椰油国小的操场,蔚蓝天空背景下,五六个皮肤黝黑的小孩,睁着亮亮的大眼睛,在操场上嬉笑打闹。
再往后,是他,准确的说,和蘭屿余文乐传给我那张照片里的是同一个人,和一位象棋大师的合照。
我的手指停在这一页,我把那张照片点开放大,仔仔细细地看着照片里他的脸。试图确认这个人真的是他。我只在晚上见过他,大多数时候,他的脸躲在阴影里面。
可是怎么会呢?我一定是记错了他的长相。如果他是那个和我下象棋的男生,如果他九年前就已经离开人世的话,我见到的……
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忘了这些照片,然后拼命想要在脑海里拼凑出我见到的那个人的样子。我回想起和他相遇的那些场景,试图寻找一些线索。突然,一副画面跳到了我脑海里。
他带我夜观生态的那晚,我们偶遇了一个会拍照的小姐姐,她提出帮我们拍照,我在她拍照时悄悄挪在了他身后。他的侧脸,一定还留在那张照片里。他就是陈逸丞吗?那张照片,也许会告诉我。
我匆忙切换到微信,划了很久才找到小姐姐的微信,问她能不能把那晚的照片发给我,很快她发了过来,那张照片上,我身子向右微微倾斜,一只手比成V字,笑的灿烂极了。而在我身旁,原本应该是他的位置,空空的,除了一睹峭壁,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再也找不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