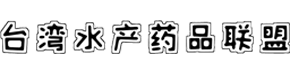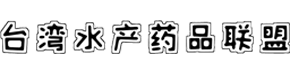可亲可爱的梅根-福克斯担纲主演了《忍者神龟》,这让人意识到三个事:
A 梅根总是在跟宅男的童年做游戏——《变形金刚》啦、《忍者神龟》啦。
B 如果不是摄像师的老婆殴打了摄像师严禁他把梅根拍得太美丽,那就是梅根疑似做了不那么成功的微整容。
C 我们小时候看的《忍者神龟》动画片里,纯良无害的女主角爱普莉尔小姐实在太邻家女子了——实际上,我们小时候动画片里大多数姑娘都很2D邻家,不像梅根这么3D火辣。
但是,嗯,等等,本篇的话题不是梅根。
2014年的《忍者神龟》里,四个忍者龟,蓝眼带使刀的那位叫达芬奇,红眼带使叉子的那位叫拉斐尔,橙眼带使双截棍那位叫米开朗琪罗,而紫眼带使棍子那位发明家忍者龟叫做多纳泰罗……到此地步,小时候看《忍者神龟》的一定会叫起来:不对啊,多纳泰罗是谁?!小时候动画片里,这位不是叫爱因斯坦么?
那,实际上,紫眼带忍者龟一直叫多纳泰罗。另外三个忍者龟分别是文艺复兴三杰,而多纳泰罗同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大宗匠。为什么叫爱因斯坦呢?因为1987年,《忍者神龟》动画片刚由北京电视台译制引进时,大家就这么称呼他了。原因?不知道。
我个人的猜测是:比起其他文艺复兴三杰,多纳泰罗实在不那么知名;为了让大家觉得“忍者龟都耳熟能详”,又考虑到他好发明个机械什么,就叫他爱因斯坦得了。
同样的与梅根有缘的《变形金刚》,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儿。Starscream怎么会被翻译成红蜘蛛的呢?Bruticus如何变成了浑天豹?Bonstructcon被译成了挖地虎。这是伟大的再创造:本来硬头硬脑的变形金刚,被上译诸位老先生一把玩,个个都戴上了水泊梁山式的绰号。习惯成自然,现在估计也没人特意去挑剔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俩名字听上去太中国范,一点儿都不洋气了。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类似的再创造,相当不少。人民现在都喜欢拿老配音翻译腔开玩笑,比如“见鬼!”“天哪!”“我向上帝发誓,要踢你的屁股!”因为这一代观众比起上一代,可说是有了相当的英文造诣,所以很知道外国人可能并不这么说话。但实际上,类似的配音翻译腔,也是一种再创造。你可以想象:童自荣老师那一代前辈们,无法用日常谈吐说话——使一口北京腔,去配罗切斯特先生,和简-爱谈情说爱,那肯定不成。所以,老配音翻译腔,尤以上译为最,是一种被重新创造过的声音:既不太像中文口语,也不太像西方口音,但能让大家接受,感觉到“对,这就是外国人说话的调调”。如果你看过《成长的烦恼》,听过野芒先生塑造的西佛尔先生,便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再对比《水浒传》里野芒先生演的林冲,自然知道声优们多么了不起。类似的例子:如果你听过《蜡笔小新》的原音,会发现矢岛晶子老师的配音很是正常,而台湾经典的冯友薇老师的配音则低沉一些,让野原新之助和幼儿园其他孩子高亮的声音形成对比,野原新之助略带猥琐的萌态,也就出来了——这种“强行制造了一个新声线”的套路,也是一种创造。
类似事儿,还不止在外语之间。熟悉TVB的诸位,一定对港片几位老配音演员耳熟能详,也一定会佩服香港的几位配音演员,既能够讲标准的普通话,又能带出清晰的香港式味道。这味道说不清道不明:商务范儿?家居范儿?总而言之,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一听就知道“那,做人要开心嘛”和“来一起喝糖水吧”的口音。
问题是这样的:
这种再创造式的传达,对原教旨翻译爱好者而言,肯定是一种扭曲的翻译。那么,这些先生们理当受到指责么?
或者,换个角度说好了:
上一代翻译者/配音演员们,经历的质疑更少,固然和上一代前辈功底扎实有关,但换个角度,上一代国人,即我们的父辈们,并没有如今的外语水平。他们欣赏着这种被再创造过的内容,甘之如饴。这一代人则已经有了足以挑刺、发现翻译不够精准的能力,但可能,我们还是得试着接受一个事实:
许多东西,也许你只能接受再创造,因为翻译是无法还原的。
字句的意思,不会在翻译中流失,但我们通常得忍受翻译腔。而音韵,除了极少数巧合,大多数是无法翻译的,而这就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六人行》里一个段子。
“She asked me if she could finish off my peanuts, I thought she said something else, we had a big laugh.
=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吃掉我的花生,我以为她说了其他的东西,我们就笑了。
如果不知道 peanuts花生 和 penis男性器官读音的话,这个小荤哏,根本让人笑不起来。翻译也翻译不了,只好加注。
,而这两者又最忌讳直言不讳。谐音是最好的表达法,很可惜,不能翻译。
翻译诗歌,更是如此: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爱伦坡的诗《致海伦》。翻译出来:荣耀希腊,宏大罗马。
但懂得英文的自然明白,这句子里面glory Greece和grandeur Rome之间的音韵对仗。
这是无法翻译的。
关于韵律,一个我举过的例子:
王道乾先生《情人》的译法天下知名,但仅论“忠实原文”,其实也未必。著名的开头:
王译: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侯,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原文:
Un jour, j'étais âgée déjà, dans le hall d'un lieu public, un homme est venu vers moi. Il s'est fait connaître et il m'a dit: "Je vous connais depuis toujours. Tout le monde dit que vous étiez bell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je suis venu pour vous dire que pour moi je vous trouve plus belle maintenant qu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j'aimais moins votre visage de jeune femme que celui que vous avez maintenant, dévasté."
挑三句标点断句有明显改变的:
Je vous connais depuis toujours. (此处直译当为:我一直认识你。王先生译: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
Tout le monde dit que vous étiez bell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此处直译当为:全世界都说你年轻时美。王先生译: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
je suis venu pour vous dire que pour moi je vous trouve plus belle maintenant qu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j'aimais moins votre visage de jeune femme que celui que vous avez maintenant, dévasté.(此处直译当为:我来是为了告诉你,对我而言,我觉得你现在比年轻时更美,比起你年轻时,我更爱你现在已经毁残的脸。王先生译: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仅看断句即知,有些地方,王先生是把从句断成了两句(比如que的几句),有些地方,则是有意把长句划开来了。这种间断,就是韵律和节奏。
而这些恰是最难还原的。
查良铮先生当年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的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实际上,细节上的自由,是因为拘束于原文,无法还原译本,尤其是音韵。
而伟大译者如查先生王先生甚至傅雷先生,就是在做再创造。
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吴启华演的方唐镜在恶搞周星驰的包龙星。举一张小的契约,一张大的契约。
国语版台词:
方唐镜:一张湿的,一张干的。大人要哪张啊?
包龙星:干的!
方唐镜:对嘛,大人还是经常叫人干爹嘛!
我小时候看,怎么都不懂。那明明是大小之分,怎么能论干湿呢?后来看原版:
包龙星:这么小的“契崽”怎么看?
方唐镜:小的“契崽”不好,还有张大的“契爷”(干爹),大人想看那一张呢?
包龙星:契爷呀
方唐镜:乖哦,大人未必不叫人“契爷”(干爹)的嘛!
对粤语观众群来说,这个包袱就流畅多了。但依次回推,可以知道翻译成国语时,必须重新制造一个包袱的艰难程度。实际上,类似的再创造最让我们熟悉的,便是周星驰那位御用配音石班瑜先生。懂粤语的朋友会一再告诉你:周星驰的原声没有那么夸张,是更冷冽平静型的调调,石班瑜的风格与他并非全然一致,所以,石先生也是重新创造了一种让我们热爱的风格来演绎了周星驰。
清朝冯班说,文章如米饭,诗歌则如酒。我借一下这比喻:好的文艺作品如酒,翻译过来也只能是米饭。而“再创造者”们所做的,是重新将之酿成酒。外语的普及降低了领会外文作品的门槛,也相应的造成了一些误会,让人低估了“再创造者们”的劳动难度,而且可以轻易的用“翻译不忠实”——比如半个世纪前丁英一先生指责查良铮先生的词句——来消解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攻击,通常来自稍微懂行,但没有到那个境界的人们。
如是,对于那些想出擎天柱、霸天虎这些译名的前辈们,那些在《成长的烦恼里》这类经典译制片里用中文营造出美国家庭氛围的前辈们,TVB那些“我下碗面给你吃好不好”的前辈们,查良铮、王道乾、王科一、傅雷先生这些前辈们,默默的承当着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接榫得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们都觉得,多纳泰罗也许本来就该叫爱因斯坦。王小波认为现代汉语是翻译家们塑造的。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这些再创造者们,制造了一种介于世俗汉语和书面汉语之间的一种存在——简单说:就跟托尔金先生创造了精灵语似的,这些先生们,重新塑造了一种说话方式。
当然也包括本文真正想致敬的人们:那些努力劳动、只在不显眼处署名、默默听译、算着时间轴、咂摸着原文意思、寻找合适的词句、偶尔耍个小机灵还可能被挑刺的、可能无意间创造了一种网络汉语语境(看各类弹幕、论坛聊天和字幕组,你会明白这中间结合得多么亲密无间),但不太会被提及的,汉化组和字幕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