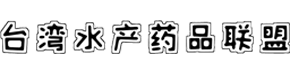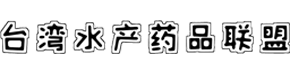那只蚂蚁在我脚背上爬过的时候停下来,咬了我一口。
这一咬,把我从本来就不深的午睡中拉了起来。细碎的草从我的头上,衣服上和手上滚落下来。那时候我的视力还不用醒来之后到处找眼镜,就看到那只蚂蚁还在我的脚上。我用两只手指把它捏住,然后放在旁边稀松的土里埋住,最后用另一只脚狠狠地踩了几下。让你丫的咬我。
我的帽子早在我坐起来的时候就从脸上掉下了。是那种农民耕作时戴的那种草帽,上于是另外一边的第三个人,也顺便就醒了。
牛在一边吃草,牛绳系在树上,所以我们也不怕丢,就放着牛在那儿吃草,我们就在这边的树底下聊了会天。一只知了很吵,一千只知了也很吵,但一千只知了会催眠,于是我们仨就都睡着了,一直到那只蚂蚁的出现。
被我的帽子砸醒的人是我的表妹,她娘给她取了个名儿叫紫菱。我妈经常说她妹妹是看多了琼瑶。我没看过琼瑶,但我看过还珠格格,所以我想我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第三个醒来的人是牛的主人,也是我们这次出来放牛的领军人物。我不知道用普通话怎么叫她的名字,在家乡的叫法直译过来,她的名字应该叫做肉鱼仔,很奇怪的名字对吧。我一开始也这么想。我们叫她用家乡话,然后和她交流又说普通话。为方便起见,我就叫她鱼仔吧。
乡下的太阳到了四五点就会开始慢慢地下沉,知了的声音也会渐渐地弱下去,仿佛它们是太阳能似的。风吹过来不像刚出来时候那么热了,我们就起身拍拍屁股开始准备回家吃饭了。鱼仔有一根细长的棍子,竖起来大概和我当时的身高差不多。她把系在树上的绳子解下来,拉了几下牛绳,对它用家乡话说“回家咯,回家咯”,那牛就不情愿地抬起头,有时候还犟着再扯几把草含在嘴里,才慢慢吞吞地跟着我们回家。有时远方看得到其他家的牛,这头牛还要哞哞几声,像是耍流氓,又像要回家的孩子跟小伙伴道别。
鱼仔很黑,很瘦,手上有很多老茧。脚上也是。乡间小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石子儿,或者是长在土里部分突出来的植物,或者风干的牛粪、鸡屎,有时候还有那种他们喝醉酒丢在半路的二锅头酒瓶子。我和紫菱都不敢光着脚走,就算是光着脚也是小心翼翼地,看着地上走一下跳一下。鱼仔不怕,她就直接光脚,也不用看地,一路啪啦啪啦就走回家了,让我们两个心里非常惊讶而又佩服。
鱼仔说她从小就这样,鞋子在家里穿,夏天不下雨的话放牛就赤脚出去,反正土地干燥不用担心脚会得病,冬天的时候有棉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她说起这个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小。外婆家那边乡下比较贫困,我们年龄又小,听着也是那么回事,就信了。
鱼仔不仅要放牛,还要分担田里的事情,和各种家务事。暑假我们回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割稻子,每天呼啦呼啦一帮人带着镰刀和竹簸箕之类的天还没亮就往田里赶,等到我和紫菱醒来,他们已经忙完一阵回来吃早饭了。
她家的厨房正对着我们家的大门,所以我们在门口蹲着刷牙洗脸的时候,可以看到鱼仔在忙活着煮稀饭,一口大锅里面白白的一片,好像一大块的馒头一样,闻着还特别香。我老是问我外婆,为什么我们不吃鱼仔煮的稀饭啊,闻起来好香啊都不像你做的一点都不好闻也不好吃。
稀饭,腐乳和咸菜,就是外婆家那儿早餐的标配了。当我还在等稀饭凉下来的时候,他们又准备去下一波收作了。
鱼仔有个哥哥,大人们叫他叫小陈,我们也就跟着叫小陈了。她叫他叫哥哥。小陈比我们大几岁,人也长得高,平日里除非要去田里做事,否则就呆在家里睡觉或者是抓一把瓜子来我家晃。
小孩子对什么东西都好奇。小陈也贪玩,经常带我们出去玩,去叫不上名字的水库游泳、用炮仗炸干牛粪,炸池塘、用竹竿黏知了然后烤着吃。这是我们每个夏天回去都会做的事情。找一根约莫四米的长长细细的竹竿,然后看谁家的檐角有好大一块的蜘蛛网,就把竹竿伸过去一圈一圈卷起来,变成一坨蛛网。等蛛网差不多覆盖竹竿最前面有十厘米长度了,我们就去找知了。这个特好找,矮小的树上也到处都是,一天下午能抓个二十几只回来。有时候我们卷蜘蛛网,还会顺带把蜘蛛卷过来,是那种跟小孩子手掌那么大的蜘蛛,拿竹竿的人就会吓得立马把竹竿丢在地上,如果前面的蜘蛛网碰到地面的尘土或者水,就不粘了,那我们就得换一个竹竿重新做了。
抓到足够的知了,我们就回家。在后院可以找到很多枯叶和木条。跟外公拿个打火机,听他说几句注意事项,嗯嗯嗯嗯地就一阵小跑去点火。等到味道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把火踩熄,从里面挑出知了来吃。
鱼仔也有带过我们去抓,但要不就是她,要不就是小陈。
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村里的人渐渐地都往外走了。打工的打工,去世的也去世了。村里开始变得荒凉,我们渐渐长大,也不再觉得小时候那些玩意好玩,也慢慢地不愿意回去了。
近来几年,我们回去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偶尔回去,鱼仔也慢慢不和我们一起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找她玩,和她聊聊天,她也是话语寥寥,好像避开我们似的。她变得更加地热衷于和那些女人打麻将,我心想这就是她选择的道路,也就不再想什么了。
去年外公七十大寿,我们暑假回去了一趟。到了的第二天,听到我妈妈和小姨说鱼仔跑了,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用“跑了”这个词去形容鱼仔,就仔细听了一下。
鱼仔原来是邻居陈家的童养媳。不知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在他家住着了,然后长大了是要给小陈做老婆的。鱼仔在两年之前就跑了,一个人去了江浙打工,今年听说还找了个男朋友,不过她跑都跑了还怎么知道的找男友的消息我就不甚了解了。小陈的爸爸和我外公聊天的时候说起鱼仔,语气里藏不住的嫌弃与愤懑。
你说我给她吃给她住,给她这么好的生活,她本来就应该做媳妇的嘛。我要报警,我要抓她回来。这个小鳖崽子。
他的脸上写着对鱼仔的厌恶,跟在他隔壁他的老婆一样,一直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外公就听着,时不时回一两句,保持微笑。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能说什么话。小陈没说话,他跟我们一起看电视,跟小孩玩麻将,谁都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鱼仔不会回来了。
人生无非一场大梦,世事莫如几度新凉。当她决定搭上江浙的火车的那天晚上,她已经不再是鱼仔,她已经成为了人生的海里,那条遮天的大鱼。
从家乡回来,很快就忘了鱼仔。心里想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童年玩伴而已。太长的人生,就如漫步在银河茫茫,遇到人便说你好再见。
直到今天突然想起,才发觉那些遇见过的人会在生命的石碑上刻下痕迹,风化水蚀不可磨灭。当你走在前方,回头一看,他们若隐若现,或许早已戴了眼镜看不太清,但依旧可以在某一个瞬间记得起来。
怎么记起来的呢。站着发呆的时候有一只像乡下那种挺大的蚂蚁路过。
那只蚂蚁在我脚背上爬过的时候停下来,咬了我一口。
妈呀真疼。